中国人的生死观:用科学的合理,掩盖文化的无能(9图)
发布时间:2017-03-28 11:15 | 来源:凤凰新闻 2017-03-16 10:58:48 | 查看:1335次
“所有看到这封信的人都是见证,你们不论多么不舍,不论面对什么压力,都不能勉强留住我的躯壳,让我变成‘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’的卧床老人!那样,你们才是“大不孝”!...好多习俗和牢不可破的生死观念锁住了我们,时代在不停的进步,是开始改变观念的时候了!”
这两天,琼瑶在facebook上发布的这封《写给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》引起了网友和书迷的很多讨论。其中,琼瑶提出了关于自己临终时的几点嘱托,希望亲人能够接受自己的自然死亡,待她病重时不要急救和悼念。

琼瑶在脸书上发布的公开信
这封交代身后事的公开信,再一次把“死亡”这件事带入了大家的视野。对于如何去迎接这生命的大限,有些常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。避而不谈,并不会改变我们终将衰老与离去的事实。
围绕着“生死教育”的种种命题,书评君专访了两位对此常年保持研究与思考的两位专家: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、《中国医学论坛报》副总编辑郑桂香。他们都谈到,琼瑶的公开信实际为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;面对死亡,现代医学不是万能的,仍然充满着局限;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共情,则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。
采写|新京报记者张畅

王一方,1958年生人,医学硕士,国内知名医学人文学者,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,《医学与哲学》编委会副主任。出版医学人文专著《敬畏生命——医学人文对话录》、《医学人文十五讲》、《人的医学》、《医学是科学吗》、《医学是什么》。
琼瑶站出来,做了很好的示范
新京报:“琼瑶事件”引发了社会对于“尊严死”的关注。从我国现有的医疗情况以及你自身的经验来看,“尊严死”的具体实施情况怎样?遇到过哪些障碍?前景如何?
王一方:“尊严死”是指在人的最后时光不把医疗目的作为首选,而是将人有尊严、有品质地离去作为主要诉求。这是医学治疗思想的很大突破,同时也减轻了家人和医生的负担。
病患的家属经常把抢救病人的生命作为“孝”的指标。而现代医学则将救死扶伤作为目标。两者都忽视了病人的尊严。无谓的徒劳的抢救,会增加病人的痛苦,这种生命的延续,其实是没有尊严和品质的,人的精神性被压抑。现代人常讲究物性的存在,而人的灵魂、社交关系、灵性的部分,却被忽视了。琼瑶能够站出来,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死亡观的突破。
我们讲,“未知生焉知死”,所以我们不对死后的世界做安排。但其实孔子不完全是这一面,他也说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闻道是他的目标,人在死之前是要闻道的。这构成了死亡的意义。琼瑶就是闻道,或者说弘道,展现了她灵魂的高度,思想的先锋和丰富。我觉得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作家往往是情感化的,她却展现了她理性和冷静的高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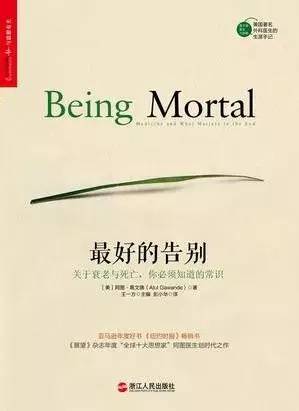
《最好的告别:关于衰老与死亡,你必须知道的常识》
译者: 彭小华
版本: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
新京报: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,让死亡的定义被颠覆了,似乎我们并没有从中学习如何面对死亡。除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,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难面对死亡?
王一方:除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,道家文化也是一例,道家讲“化蝶欲仙”,怀抱两个梦:神仙梦和侠客梦。两者对死亡有隐形的抵触,“仙”作为永生的概念,其实还是将人视作肉身的存在,抵触死亡。道家中,庄子对死亡是比较潇洒的,但庄子在中国文化中比较边缘,成功人士不信他。他老婆死了,他鼓盆而歌,人们却带着戏谑去看他,似乎他对死亡的态度不够神圣。老子呢,死亡则是很神秘的,过了函谷关,就湮没在黄沙中了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也是在讲死亡,到了桃花源,时间和身份丢失,这和死亡是很像的:建立了新的身份和环境,和之前的世界断裂。庄子的《逍遥游》,其实也是诗化地讲死亡。很多中国文化的巅峰体验,也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,高兴死了,快乐死了,幸福死了。中国人对死有决绝和潇洒的一面。
今天的中国文化,受西方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,技术崇拜、财富崇拜。我们恐惧死亡,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实的东西在牵扯我们。花钱买命的想法,其实是现代性的对生死的误解。在西方,这一块是靠宗教来平衡的,如果高财富的社会不能用宗教来平衡,人是会走火入魔的。毕竟高财富是无法替代宗教的。
我们不要把死亡教育归咎于古人和先民没有给我们树立榜样。《淮南子》中的“大禹治水”讲,龙王来翻大禹的船,威胁他,大禹站在船头大喊:“生寄死归。”死才是归途,和海德格尔的“向死而生”是一个概念。
我们现在只是做了简单化的处理,认为文化基因里没有死这个概念,其实今天我们生死观的扭曲和异化,是受功利主义文化、无神论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果。
生死教育要循序渐进
新京报:你曾说:“医疗观要调整,要把痛苦的接纳和对生死的豁达包含进来。”就这两方面(接纳痛苦、对生死豁达)而言,就你的临床经验来看,我们的现状是怎样的?
王一方:在今天的医改格局中,老百姓是技术主义,医生是科学主义。医生往往会用理性的、教科书式的语言谈论死亡,不会和病人探讨文化语境的死亡,医学院的教育也缺乏这样的语境。所以医生在这方面,话题储备是不足的。我经常和医生说,你可以不谈宗教信仰,但你可以谈民间信仰,比如对病人说:“去见马克思”,这也是一种归宿。我去探望过一位老农民,他没有文化,也不懂哲学,我第一句话说:您受苦了。他说:我今天受苦,是为了祖孙后代消灾。他将吃苦的合理性建立起来了。我们今天则用对抗来看待痛苦,比如注射吗啡。其实是用科学的合理性,来掩盖文化上的无能。我当时和老农民说:您的病可能治不好了。他说:我的父辈都去天国报到了,我也要开始报到了。他将死看做归宿。在他看来,死就是在新的地方和人会合了。为什么范用先生不愿意接受治疗,他的理由是:我认识的人都走了。我觉得讲的特别好。死就像排队一样,你不能插队,也不能申请靠后。
毕竟,中国人的道德感就是通过死亡建立的,在死亡面前才彻底决绝、没有退路。我们没有死亡的文化,就没有自我审判的过程。
新京报:我们今天的健康教育除了教大家吃什么、喝什么、怎么锻炼之外,没有将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囊括其中,导致无论是病患还是亲属,在面对疾病或死亡时难以接受。按照你的经验,应该如何对大众进行“生死”相关的健康教育呢?
王一方:教育这个词有点飘,教是用知识告诉他,育是精神的培育。今天的健康教育有两个概念:第一,一切医学的传达都是为了维护健康,只有“人生观”,没有“人死观”。其实,我们的健康应该包括它的反面:比如疼痛,残障,衰退,死亡。而我们都没有。谈完健康,谈痛苦、失能、残障、死亡。而我们现在直接推到死亡教育,有点残酷。死亡教育,或者说生死教育要循序渐进。有正常就有意外,健康是正常,“健康教育”四个字就有些自欺欺人,“生命教育”就好很多,包含健康,也包含它的反面。所以我建议,把“健康教育”改成“生命教育”、“生死教育”。毕竟,中国文化是一个崇尚快乐的文化。
第二,教容易,化很难,后者要体验,要演习。做成光盘、做讲座,是没有用的。活人办一次丧事,参观一次火葬场,孩子去读生死电影和绘本,都是必要的。育是很重要的,是培育、开化。怀特讲生死课,说人就是被上帝唤起来的泥土。有一天你倒下了,其实就是回归泥土。没有什么好悲哀的。

《生死学十四讲》
作者: 余德慧 / 石佳仪
版本: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1年4月
新京报:北大医学院是如何培养学生对于痛苦和死亡的认知,对未来的医生进行“死亡教育”或“生死教育”的呢?
王一方:其实我们做得还不够,虽然我们开了生死的讲座,但是毕竟这些孩子还是青春年华,青春年华本身就和死亡形成巨大的落差。我们作为老师,有两个苦恼:在他们青春的时候,讲死亡,很残酷;在青春靓丽的时刻,忙着谈恋爱、熬夜,对死亡没有体验,其实讲起来效果并不好。所以我和学校领导建议,和声光电磁做研发,用机器演示和模拟疼痛,让学生去体验。《疼痛的隐喻》里讲:“疼痛像烧红的铁。”机器可以模拟这种感觉,等于说是将死亡的感受具象化。还有比如失能,让你喝水,但手抬不起来;让你跑步,但是脚很重;看东西,前面的东西都在晃;让你闻,别的气味在干扰。最后一步就是死亡的体验。美国有一种宇航员的飞行模拟器,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器械,造成人身份的丢失,通过这个器械让人去感受死亡。
我们也会让学生们去回忆亲朋好友的死亡,让他们达到一种共情。生死无常,我常和我的学生说,不是说你年轻,就一定比老人活得长。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,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。活就要有品质。上帝让你坐起来,就要有坐起来的光彩。
对于生命教育,我们也很苦闷,尽管知识方面已经做了很多,但精神发育还是做得不够,怎么样融会到他们的生命中还是一个课题。
医生的道德感,往往需要生病才能被唤醒
新京报:2013年,在你的著作《中国人的病与药》中,提到了“疾病”和“疾痛”的区别。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下,你所专注的领域“叙事医学”中,是如何缩小或弥合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的?培育医生与病患的情感共同体,有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,可以供我们借鉴?
王一方:叙事医学中,疾病是有文化病因的。身体受到打击之后,除了蛋白质、肌肉、骨头的损伤之外,还有心理、灵魂、社会关系的投射。所以健康,在叙事医学中,应该是“全人”的健康。疾病也一样。疾病不仅仅是躯体的疼痛,还有心理的投射、社会关系的破裂等。医生想要理解这一点,是很容易的。方法一:他的家人有人得病,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,当病人是你的亲人的时候,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方法二:医生自己也会生病,叙事医学说:“脱掉白大褂,换上病号服。”换上病号服分为两种:第一种是假换,在你没生病的时候,去病床上躺着,你会感觉到人间冷暖;还有一种是真换,这样你才会换位思考。医学人文,是生命的体验,是默会知识,不需要教的。为什么我们看病喜欢找老医生,因为他们对于生命的体验随着工作、生活经历的积累,会焕发出人文的情怀。他们会有一种觉悟。
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,涉及整个社会的链条,但医生是第一链条,你对病人好了,传递下去,整个社会就好了。医生的道德感往往通过生病才能被唤醒。生过病的医生,才能达到这种高度,给人真情。

《中国人的病与药:来自北大医学部的沉思》
作者: 王一方
版本: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年7月
新京报:目前医患关系依然是大众热议的焦点。医患关系的紧张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呢?目前有哪些办法可以有效缓解呢?
王一方:病人和医生,一个站在悬崖边上,一个没有站在悬崖边上,后者就不知道前者那种痛苦。这比科学上学会哪个神经递质作用于哪种神经递质,要重要很多。将来的医患关系,要通过虚拟痛苦来拉平,只有这样,才能让医生进入苦难的峡谷,不然让他站在那里同情你,其实是道德伪善。今天我们讲中国的文化一定要“练真的”。对穿越痛苦、死亡都没有体验,再谈道德,其实是徒劳的。叙事医学就是通过小说、电影,进入死亡的体验,训练你的共情机制。但今天的医生不愿意看小说,也没时间看小说,只看参考书、教科书。我哥哥是个外科医生,他说好的外科医生要练琴,练细腻、练感情;练书法,练战略布局,每一笔从哪里下。
现在呢,我们一方面让学生们拼命练,一方面让他们产生厌恶,最后变得目中无人,他自己就产生逃避心理。医患关系怎么会好?
再一个,现在很多患者的生死观也有问题,认为一切死亡都是非正常死亡。认为自己花了钱,没能挽回一条命,不能理解,而让医生置于悬崖边,甚至危及医生的生命。
对于老百姓来讲,认命是很难的。比如“魏则西事件”,魏则西说让父母生个试管婴儿,父母岁数很大了,就去尝试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蛮性的文化、崇拜的文化所造成的。豁达教育从生死开始。在死亡面前思考,就是对生存的思考,终极的思考,人为什么活着,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。
生死教育是一把钥匙,不仅可以开临终关怀的门,也可以开医患关系的门,当然更重要的,是打开对于生命与死亡的认知与理解。

郑桂香,《中国医学论坛报》副总编辑。
疾病防控应当前移
新京报: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,让死亡的定义被颠覆了,似乎我们并没有从中学习如何面对死亡。你认为为什么我们这么难面对死亡?
郑桂香: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所致,觉得人死了,是阴阳两隔,是在“地下”受到折磨,是痛苦的。另外临死前的身体疼痛也让人格外痛苦。加上死亡教育的缺乏,让死亡本身的恐怖意味更浓了。如今医学发展,科学进步了,我们其实在缓解患者痛苦方面有很多方法,可以让他们平和安详地离开人世。
就我的这些年观察来看,随着媒体、公益组织、医学专家的积极推动,随着社会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人能坦然面对死亡,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能理解,我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,都在慢慢学习,慢慢转变。

《死亡如此多情: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》
作者: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
版本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7月
新京报:我们经常说要培养医生的人文关怀,让医治病患,特别是临终关怀更有温度。从现有的医院体制下,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呢?
郑桂香:去年的“魏则西事件”给我的印象很深。当时很多人都在谴责那家医院和他们无效的疗法。但从另一个角度想,在面对目前的医疗水平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时,我们应该如何面对,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作为医生,当我们面对患者时,有责任和义务让他们正确地认识疾病。在现有体制下,有专家做过大致的统计,人的一生,医疗上花费的70%-80%都用在生命最后的两周。但事实上,最后的花费是徒劳的,如果把这笔钱转移到预防疾病上,就可以大大改善健康状况,降低无效医疗的花费。我们国家提出的“人人享有健康”,就是让老百姓对健康有更多的认识,把疾病防控前移。
新京报:当下医患关系依然是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,从医生的角度,您认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有哪些?以你作为医生的经验,有没有什么切实的办法可以有效缓解这种紧张?
郑桂香:一定有医疗体制的问题,这是不能回避的。从我的角度来看,原因第一是医学信息不对等。第二是,医患双方都应该换位思考。我们前年出版了一本书《真情沟通》,讲述的就是患者和医生之间的故事。有一个故事很小,但给我的印象很深:一位年轻的医生,在医院门口碰见一位老人,问他检验科室怎么走,他先指给她,穿过这个楼,过了那个门,怎么转弯。他刚要离开,看见老人还是很迷茫地站在原地。于是他就亲自带老人到了那里。他说想到了自己的奶奶,到一座陌生的城市,一个不熟悉的医院,要去检查,却找不到,该有多无助。这就是医生和病患都应该养成的共情能力和换位思考。

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
作者: [美] 保罗·卡拉尼什
译者: 何雨珈
版本: 猫头鹰文化·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2月
提前做选择,琼瑶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范例
新京报:近几年,高校和社会都开始关注“死亡教育”和“生死教育”,关注人们对于痛苦和死亡的理解和认知。以你的观点来看,我们为什么要进行“生死教育”?在医科大学的教育体制和日常授课中,“生死教育”是如何进行的?
郑桂香:现在的医学院都要教育未来的医生:要有对死亡的正确认识;要了解患者面对死亡时,他们的情感是如何变化的;医生要适当帮助患者去面对无法避免的事情,让患者慢慢接受它。让患者感觉到医生就在他身边,并没有因为疾病不可治而抛弃他。《死亡如此多情》2013年出版后,北大医学部的人文学院把这本书作为教材,让学生们去学习,写读后感。王一方老师给我发过来学生们写的读后感,能够看到他们对于死亡的思考和感悟。天津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。
而刚刚谈到临终关怀,中国能够做到的机构还是远远不够的,原因之一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医务人员是很缺乏的。

《恩宠与勇气:超越死亡》
作者: [美]肯•威尔伯
版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6月
新京报:这次的“琼瑶事件”让“安乐死”再度回到大众视野。在法理上,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;而在伦理上,“安乐死”则有悖于生存权利。在我们国家,实施“安乐死”的阻碍有哪些?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?
郑桂香:琼瑶提到的不是“安乐死”的问题,“安乐死”是到了临终的时候,让医生通过用药协助死亡的过程。而目前公益人士倡导的是“尊严死”,病人自己可以选择抢救和不抢救。这一点是需要澄清的。我们现在谈的更多的,其实是“尊严死”:通过一些方法,比如让周围的环境更安静,或者适量用一些吗啡,缓解病人的痛苦,而不是安乐死。
这一点在大陆推广的难度的确很大,台湾现在做得不错。原因可能大陆人们固有的传统理念,病人的家属大多不愿意放弃,认为任由病人去死,和科技的发展相背离,科技都这么发达了,怎么能放任不管呢?“尊严死”更多的是给病人和亲属多一种选择,但因为道德伦理上很难接受,所以家人不容易做到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所以我们就需要病人自己清醒时,在有行为能力的时候,提前做出选择,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生前预嘱”。琼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。
延伸阅读
听了两位专家的解读,相信你对衰老跟死亡,有了更勇敢的认识。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,避讳谈论死亡,但在中文出版界,翻译也好原创也好,我们 已经能读到很多优秀的谈论生死教育的图书。
以下,是书评君选取的几段谈论生死问题的书摘。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解,你可以在文末继续阅读书评君的“死亡教育课”专题。
1
我草草浏览着眼前的 CT 片子,诊断结果显而易见:肺上布满了数不清的肿瘤,脊柱变形,一整片肺叶被侵蚀。这是癌症,而且已经扩散得很厉害了。
我的肺癌确诊了。人生本来有那么多计划,那么接近事业巅峰。现在体力不支,重病缠身,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倒塌。面对我的病人曾经面对过的,有关「存在」的窘境。
......
早上我在疼痛中醒来,除了吃早餐,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
我无法前行(坚持不下去了)!我心里这么默默想。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反对,「你仍将前行。」
这句来自塞缪尔 · 贝克特的话,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,这个时候适时地冒了出来。
我下了床,向前一步,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:「我无法前行。我仍将前行。」
就在这个早上,我作出一个决定:我要逼迫自己,回归手术室。为什么?因为我做得到。因为那就是我。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。
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,我仍然还活着,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。
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
作者: [美] 保罗·卡拉尼什
译者: 何雨珈
版本: 猫头鹰文化·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2月
2
我想,大多数在医院里面离世的病人都是痛苦的,这种痛苦常人无法想象。插管,心脏按压下去5厘米(这样才算有效)的那种感受,正常人永远没法体会到。死是一种必然的状态,让死者走得更有尊严,痛苦更少一点,是活人应该尽的一项义务。一个健康的人、有清醒头脑的人,应该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,只有活人做好了,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。
“To be or not to be,that is the question.”(生存还是死亡,这是一个问题。)是哈姆雷特的经典名句,其哲学化命题是每个人随时面对的,即使是当生命走到尽头。面对生死,有人选择坚持,有人选择放弃;有些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,有些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;有些选择是患者或家属的决定,有些选择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体现。坚持还是放弃?这是我们面对生死最先发自本能的反应。无论何种选择,都与对错无关,那只是一件人间往事。
病人死于治疗本身,跟他(她)死于疾病的复发,医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……医学上,有时候,追求一种极致,也会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比方说手术,一个肿瘤切得差不多,可能能多活两年,但医生想做得更完美一点,想切得更干净些,却发生了手术意外。其实治疗越充分,复发概率就越低,但发生治疗相关事件的概率也就越大。如何平衡,这个度怎么把握,确实很难。因为这些都是未发生的事情,医生不是神,预测不到后面的结果。
《死亡如此多情: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》
作者: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
版本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7月
3
1991年,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镇,当地的医疗界领导引领了一场本系统内部的运动,让医务人员和病人讨论临终愿望。几年之间,这已成为所有入住医院、疗养院或者辅助生活机构的病人的一项常规项目,他们同富有这类谈话经验的人坐下来,完成一项浓缩成4个关键问题的多项选择表。在生命的这个时刻,他们要回答以下4个问题:
1.如果你的心脏停博,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?(单选)
2.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?(单选)
3.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?(单选)
4.如果不能自行进食,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?(单选)
到1996年的时候,这个小镇的居民中,85%的人都填写了一份这样的书面生前声明,医生几乎了解每一位病人的指示,并按照指示办。
“生前预嘱”远不止这一个地方有,现在很多医院和病人都在探讨这个问题。
《最好的告别:关于衰老与死亡,你必须知道的常识》
译者: 彭小华
版本: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




发表评论
网友评论
查看所有评论>>